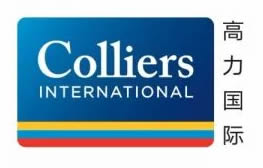“只有铁,只有血,只有铁血可以救中华,誓把倭奴灭……”这悲壮激越的战歌,是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由东北沦陷区爱国青年逃亡关内唱出的团结一致、收复国土的心声。
一九三四年和县来了一位青年县长,名叫刘广沛,二十五岁,辽宁人,学生出身。消息一传开,茶坊酒肆议论纷纷,有人说:当官的应该有点派头,从来未听说一个父母官上任这么清清冷冷;也有人说:年纪这点大,又是洋学生,肚里没有几点墨水,能当官吗?还有人说:这清官,要真能“官是人民的父母,人民是官的赤子”就好了;另有一种议论是什么当官不当官,不过来搞钱罢了,“一任新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嘛!
刘广沛从关外到关内,出任和县县长到底怎样?下面介绍两则故事。
抑制豪强,扶助贫农
刘广沛到和县,不是挂牌那天才到任的。他早在两月之前就踏遍了和县的山山水水、村庄集镇,对百姓的生活生产、风俗习惯,都已了如指掌。他到处都听到“要想和州好,先拔大毒草”的民谣。从中他归纳出一句话:权势欺人太甚。这“大毒草”是谁?就是当时和县的几位豪强户。这几位为首的有权势的富户,除拥有大量土地、多所市房外,还经商投机,放高利贷。不少人上有靠山,下有打手,气焰冲天,炙手可热,历任县官只能视其脸色办事。刘广沛县长到任时正值催粮紧迫季节,四门之外,每天均有兵丁抓人,押交田赋。这些人大都衣衫破烂,手胼足胝,面有菜色,哀叹连声。一天刘广沛亲自询问几位被押者,原来都是只有少量土地的贫苦农民,因家口繁、欠债多、租利重、年岁欠收,无力交纳田赋。刘县长把管田粮的负责人找来,要他们把历年欠田赋的名单和土地数全部抄报。这一下就发现了包括“大毒草”在内的一些豪强户多年未交田赋。刘县长不禁喟然长叹:关外沦陷区人民遭受亡国之痛,希望关内官民能奋发图强,团结一致,收复失土。似此哪有富国强兵之望?他决定树正气、压倒歪风,扶国本、打击豪强。于是刘县长将他们一一抓来。开始“大毒草”等人还满不在乎,认为自己错节盘根,谁也没法,这不过是新官上任三把火,摆摆威风罢了。便或以势恫吓,或暗中说情,甚至公开行贿,企图缓和紧张局面。可是这一切的一切刘县长概不买帐,这些人蕞后只得交清了田赋款。这一声霹雳,全县震动。很快城乡各地邪气降服,县库富裕。为了扶助贫苦农民,刘县长又将全县农民所欠田赋一一清点,提出三条措施:有能力交的交;交付能力小的酌情交;真正交不出的免交。广大贫苦农民欢声不绝,额手称庆,有口皆碑,纷纷赞颂刘县长除暴安良的政绩。
调查访察,明断父子案
注重调查访察,是刘县长理政的又一特点。一天,刘县长接到一张父亲控诉儿子不赡养的诉状。当时司法未独立,案件由县长充当承审员审理,他看了看诉状,便单身微服前往那个地方,经多方调查、反复核实,总的内容是:当父亲的小时候家里生活条件好,又无兄弟姐妹,是独生宝贝,父母特别溺爱,一贯放荡任性,追求享受,不事生产,还染有不良嗜好,抽鸦片,好赌博。儿子还未长大,家里财产就被他败光了。儿子从小放牛,长大打长工,非常穷苦,还是一位亲戚把女儿与他配成夫妻,生有子女四人,都是黄口稚子。一家七口,全靠他夫妻俩种田养活。因此对父亲奢侈生活无力满足,以致父亲不满。刘县长得此实情心中早已有数了。那天快近中午开庭时,原、被告均到庭候审。当刘县长询问原、被告姓名和住址时,早看出父亲是一个“斯文”架式、骄生惯养、好逸恶劳的人。儿子呢?年只三十二岁,面色苍老,粗手粗脚,一眼就看出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。刘县长灵机一动说:“至亲莫如父子,父子打什么官司?!好吧,现在已是中午时分,你俩上街弄点吃的,下午再来。”说罢,叫左右拿两吊钱一人付给一包(当时一包是一百枚铜钱)。父子接过钱分别上了街。父亲有钱在手就大而花之,坐在酒馆里要酒要菜。儿子呢?一面看着县长给的钱,一面摸摸自己的肚子,只在街上买了一块大饼充饥。下午开庭时刘县长问:“你俩都吃饱了吗?”两人同时回答:“吃饱了。”“钱够不够?”“足够、足够。”“剩下的钱都还给我吧!”父子分别把剩下的钱交上公案。一数,父亲用了八十五枚,儿子才用掉五枚。刘县长风趣地说:“父亲上了年纪,身体又不强,吃的钱却是儿子的十七倍,好大的饭量呀!这样大饭量的父亲,就连我当官的虽然有一定的薪水(工资),也养不起你啊!”父子两人一听都哑口无言。刘县长经过细致询问,父亲浪费,儿子节约,真情实况已无遗。便对那父亲作出了批评,劝其儿子今后仍按家庭生活水平赡养父亲。并向父亲晓以大义,以后应体谅儿子负担重,确实无能力供你无度挥霍,自己也应当节俭才是。然后宣布退堂。一场父子纠纷就这样了结,一时传为佳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