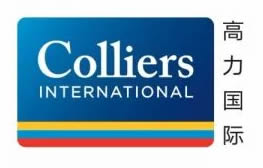不知是哪个朝代,和州出了个叫贾举的县官。其人仪表堂堂,举止端庄,少承儒训,一举登科,年方弱冠便平步青云直上,被皇上授为和州的大尹。他少年得意,十分地矜持,自以为学业淹贯古今,才智过人,便每于人前自诩曰:“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,我贾某自幼饱读诗书,诸子百家,无不通晓,四书五经,倒背如流,治理一个小小的州县嘛,岂不易如反掌?”
贾举在和州一上任,便晓谕合府上下,一应大小纠纷,任何疑难案件,皆要唯夫子之言而行,唯圣人之语而断,绝不越雷池一步。凡夫子没讲,圣人不做的事,一概不予审理!
一日升堂理事,公差押了个偷席子的人上堂。偷席子的人名叫赵文,住在本州城南赵庄,老母年逾古稀,长期卧病在床,家徒四壁,母子相依为命,全赖赵文帮工维持生计。赵文生性至孝,时届隆冬,风雪漫天,怕老母身受风寒,为遮破屋风雨,他在主人家暗暗地(偷偷地)带了一床破旧的草席回家,因此被告发到官府。
贾举问明案情后,不知如何发落是好,便闭起双眼摇头晃脑地把大学、中庸、四书、五经统统背诵了一遍,突然他眼睛一亮,找到一条“根据”。只见他把惊堂木一拍,大声喝道:“来人呀,把赵文推出去斩了!”赵文一听,魂飞魄散,苦苦求饶,两旁人等无不瞠目结舌,感到量刑过重,齐声要求从轻发落。贾举怒不可遏,厉声斥责道:“尔等无知,休得胡言!你们岂不闻夫子云:‘赵文盗席(朝闻道夕)死可矣’,赵文盗席犯的是死罪,夫子这么说了,我们这些身沐皇恩的儒家子孙,还能不照此办理吗!这是丝毫违拗不得的!”众人听后,面面相觑,屈死了这个仅仅拿了一张破草席的赵文。
事有凑巧,三天后,城里夫子庙里的一口铜钟又被人偷盗了,案子报到衙门后,贾举惊慌失措,勒令捕快限期破案。不到十天,盗钟的首犯陈某被拘捕归案了。合衙人等,比照上次案情,都以为这次事态严重,陈某是必死无疑的了。但却怪,这位贾大老爷经过一番念念有词之后,蕞后一反常态,和颜悦色地当众宣判道:“把他放了!”众人惊诧莫名,追问其故。贾举扬了扬眉毛,慢条斯理地笑着说道:“君子之盗钟(道忠)恕而已矣!君子盗钟,圣人都说‘恕而已矣’,何况他这个小小的陈某?”众人听后岂敢违抗,只好把这个陈某一放了事。可是案子并没有因此了结,贾举却派公差把夫子庙里的一个叫做邦军的小管事拘了来,要问他一个“管理不善”之罪。邦军拘到后,贾举笑着向两厢说:“我乃朝廷命官,幼受儒学,少被皇恩,岂能离经叛道,不依圣人之言办事?”说罢,喝令衙役寻来一根又短又粗的圆木棍,硬要将这个“管理不善”的邦军用刑。众衙役见现放着的木板不用,却偏偏要找来一根圆木棍用刑,都不知如何用法。贾举大声喝道:“混蛋,糊涂的东西!这圆木棍不是树做成的吗?子曰:‘邦军树(邦君竖)塞门’,他不正是叫邦军吗?把他裤子扒下,将这根圆木棍往他屁眼里一塞,不就完了!”众衙役啼笑不得,正欲动手用刑,邦军磕头如同鸡食米一般,哭着申辩道:“青天大老爷,‘邦君’是官啊,我名字叫邦军,不是真当了‘邦君’这个官啊!我只是夫子庙里的一个小管事的呀!大老爷要明察,开恩啊!”贾举一听哈哈大笑道:“这就更没错了。你看,夫子说得很明白:‘邦军树(邦君竖)塞门,管事(管氏即管仲)亦树(竖)塞门’嘛。塞你什么‘门’?还不是塞屁眼门!”邦军有冤难说,无言以对,两旁明知错判,也不敢据理力争,生怕老爷又胡乱地背出一段什么夫子的话来,惹得一家老小身家性命难保。只得依令而行,结果活活地塞死了这个无辜的邦军。
贾举上任,未及周年,全县盗贼蜂起,民怨沸腾,虽白日行奸,公开抢劫,亦无人敢讼。贾举沾沾自喜,自以为夜不闭户,道不拾遗,天下太平,牧民有方,不负圣恩浩荡,居然为朝廷擢迁旌表,成为一位远近闻名的“清官”。谁料泰极否来,不多久,这位自鸣得意,飞黄腾达的“青天”大老爷,却在后脑勺上害了个“对口”,终日脓血不止,痛不欲生,虽遍请名医,始终未能治愈,贾举正在日夜呻吟,痛苦万状之际,一日有个须发如银,面目清癯的长者跑上门来了,口称世代名医,能治百病,任何疑难杂症,一经过目,便妙手回春,药到病除,自告奋勇地要给贾举看病。贾举欣喜异常,连忙打恭作揖,请教长者要以何术而治?长者看过患处,神情肃然,故作紧张地说:“公之疾已入膏肓,不锯颈以李木接之,绝无生望也!”贾举大骇,惊问曰:“长者如此治法,夫子说过无(没)有?”长者曰:“我祖承儒教,幼读经史,非圣人之言不为治也,绝不敢胡作非为。”贾举仍恐没有出处,又追问道:“夫子究竟是如何说的呢?”长者说道:“夫子曰:‘不以李接(礼节)之亦不可行也’,故锯颈以李木而治之,这是万无一失的!”贾举听后频频点头道:“这就是了,这就是了,既然夫子这么说了,那就是真理,你就照此而办吧!”于是这位长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,断然地锯下了这颗非圣人之言而不行的榆木脑袋。